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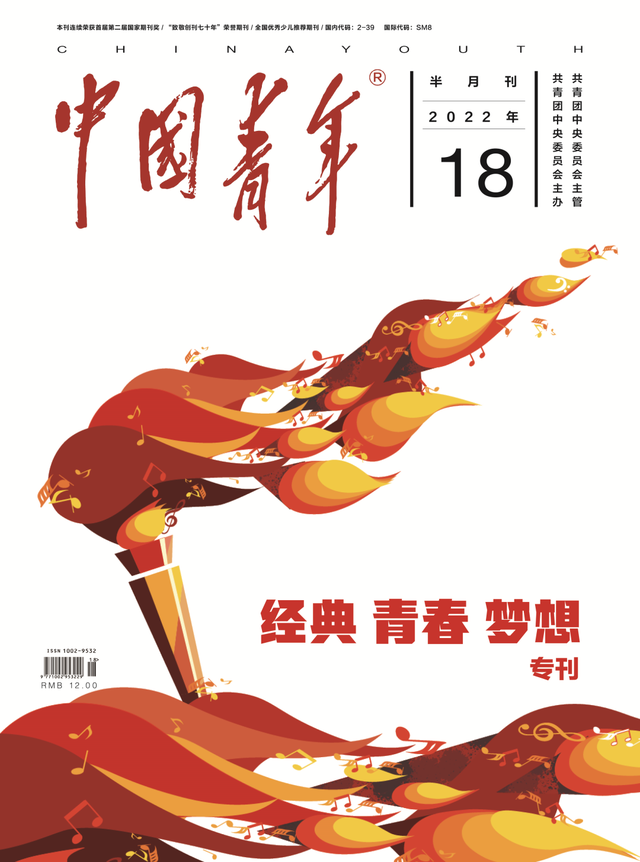
楊一博:“時代給了我一支筆”
文-王渝 張寶瑞
 2021年9月,楊一博(左)同中國音協(xié)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張千一等詞曲作家一行在新疆采風(fēng) 成長于一個普通的家庭,從東北考到北京,自中國音樂學(xué)院附中畢業(yè)后,在中央音樂學(xué)院師從唐建平教授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學(xué)習(xí),隨后進(jìn)入中國音樂學(xué)院學(xué)習(xí),師從趙季平先生,成為他的首位作曲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多年來,一路努力、向上成長的“80后”作曲家楊一博在多元類型的音樂創(chuàng)作、大體量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累積中保持著創(chuàng)作的好奇與嘗試,不循規(guī)蹈矩,不斷突破、創(chuàng)新、調(diào)整,以作品回應(yīng)著時代之問,一部部極具民族風(fēng)格與時代特色的作品反映了他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作理念:“我來自普通的人群,更能理解那些形形色色、可愛可敬的普通人;我的音樂就是體驗真善美,描繪普通人的人性的光輝,‘為人民抒情’是我自覺的選擇。” 以下是楊一博的講述。
2021年9月,楊一博(左)同中國音協(xié)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張千一等詞曲作家一行在新疆采風(fēng) 成長于一個普通的家庭,從東北考到北京,自中國音樂學(xué)院附中畢業(yè)后,在中央音樂學(xué)院師從唐建平教授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學(xué)習(xí),隨后進(jìn)入中國音樂學(xué)院學(xué)習(xí),師從趙季平先生,成為他的首位作曲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多年來,一路努力、向上成長的“80后”作曲家楊一博在多元類型的音樂創(chuàng)作、大體量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累積中保持著創(chuàng)作的好奇與嘗試,不循規(guī)蹈矩,不斷突破、創(chuàng)新、調(diào)整,以作品回應(yīng)著時代之問,一部部極具民族風(fēng)格與時代特色的作品反映了他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作理念:“我來自普通的人群,更能理解那些形形色色、可愛可敬的普通人;我的音樂就是體驗真善美,描繪普通人的人性的光輝,‘為人民抒情’是我自覺的選擇。” 以下是楊一博的講述。
? +
+
“追求真、善、美是我的創(chuàng)作動力”
如何展現(xiàn)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勤勞樸實、真誠善良的可愛人民?如何在音樂中表現(xiàn)他們的憂愁、喜悅、歡樂?如何捕捉記錄人性的閃光點(diǎn)?這些都是吸引我不斷深入探尋的創(chuàng)作動力,在對每一部作品的探索中,“真、善、美”始終是我追求的創(chuàng)作主題。 我很榮幸能成為趙季平老師的學(xué)生,跟隨老師學(xué)習(xí)作曲。我還記得在趙老師第一堂課上,他拿出幾首自己以李白詩歌為題材創(chuàng)作的音樂作品,讓我進(jìn)行配器,在我對作品進(jìn)行分析并完成配器后,老師耐心修改指導(dǎo),這實際上是一種啟發(fā)式的教學(xué)。在錄音中,趙老師很尊重年輕人的想法,并根據(jù)我的思路給出許多完善的建議,讓我獲益匪淺,也深受感動。在跟隨他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我深受影響,也逐漸理解鮮明的主題決定著音樂的氣質(zhì)和風(fēng)格,而結(jié)構(gòu)令音樂表達(dá)更完整,后來我對民族音樂和流行音樂的融合創(chuàng)作,也是得到了趙老師的啟發(fā)。 2021年,我參與了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的音樂創(chuàng)作,寫出了《我的父親》《喜淚》《父親的嗩吶》《跪別》等音樂作品。電影中,音樂作為電影語言的補(bǔ)充,輔助劇中人物表情達(dá)意,烘托故事情感。 我的作曲配器運(yùn)用了鋼琴、嗩吶、竹笛等,同時穿插民樂、弦樂、女聲吟誦等來表現(xiàn)人物從克制到爆發(fā)的遞進(jìn)式情感。在焦裕祿書記與娘親分別的時刻,音樂成為焦裕祿不舍告別母親的情緒宣泄;結(jié)尾時,以女兒焦守云的女聲訴說視角唱出對父親的思念,同時,女聲也代表今天的我們來紀(jì)念為蘭考縣脫貧發(fā)展鞠躬盡瘁的焦裕祿書記,娓娓道來“好干部”的動人故事。 創(chuàng)作亦是學(xué)習(xí)精進(jìn),在音樂結(jié)構(gòu)和形式上,我希望不斷實驗、改編、創(chuàng)新,讓形式新穎有趣,結(jié)構(gòu)豐富完整,來表達(dá)我所理解的“中國故事”。
? +
+
時代更替,推陳出新
近些年,我跟隨中國文聯(lián)、中國音協(xié)、中國文藝志愿者協(xié)會組織的文藝志愿服務(wù)活動,走進(jìn)了重慶、西藏、海南等許多地區(qū)和縣市。這些地域的民歌文化、多彩的鄉(xiāng)間風(fēng)貌和淳樸的民風(fēng)點(diǎn)燃了我的創(chuàng)作靈感。在廣闊美麗的中國大地上,我汲取著不同地域豐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樂的養(yǎng)分,訴說著時代之音。
2020年,我參與了北京民族樂團(tuán)民族管弦樂組曲音樂會《中軸》的創(chuàng)作,提交了作品《水潤萬寧》。萬寧橋是我中學(xué)記憶里的標(biāo)志性建筑,少年的我無數(shù)次經(jīng)過這座位于北京中軸線上的橋,莊嚴(yán)的皇城建筑連接著北京市井的煙火氣,恢宏莊嚴(yán)與古樸溫潤兩種氣質(zhì)交融于一拱橋間,這兩種氣質(zhì)如何用音樂來展現(xiàn)?民族與流行的碰撞將歷史與當(dāng)下連接,這是我對改編創(chuàng)新的一點(diǎn)體會,包括后來我參與創(chuàng)作的舞劇《英雄兒女》,民族交響音畫《孫子兵法·回響》亦是如此。
2018年,我參與到由中國文聯(lián)和中國音協(xié)共同主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型原創(chuàng)交響合唱《奮進(jìn)新時代》的主題創(chuàng)作中。和老中青三代優(yōu)秀的音樂家們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zé)任感,潛心創(chuàng)作、傾情奉獻(xiàn),將中國傳統(tǒng)音樂元素、地域民族風(fēng)情和當(dāng)代中國音樂表達(dá)有機(jī)地結(jié)合,既是創(chuàng)作,又是學(xué)習(xí)。
在幾次改稿會中,著名作曲家印青老師等經(jīng)驗豐富的前輩藝術(shù)家們,為我們青年創(chuàng)作者保駕護(hù)航,不僅尊重、包容我們的創(chuàng)作想法,對原創(chuàng)歌曲一首一首地進(jìn)行細(xì)改分析,而且在修改的過程中又傳授給我們很多專業(yè)技巧。參與這樣的主題創(chuàng)作,讓我更深入地了解到民族的語言和調(diào)式如何與當(dāng)下流行的音樂語言相結(jié)合,這次實踐也為我打開了“直抒胸臆”這一音樂抒情方式的大門,最終創(chuàng)作出女聲獨(dú)唱《奮斗才有幸福來》。
? +
+
歌聲悠遠(yuǎn),同頻共振
經(jīng)典是歷史之鏡,鐫刻民族之魂。經(jīng)典的音樂主題歷經(jīng)時間的洗滌,浸潤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田。回望歷史,一代代革命先輩對祖國的熱愛和舍生取義、敢為天下先的英勇豪情猶在眼前。對經(jīng)典作品的創(chuàng)新,表達(dá)了身處新時代的我們對歷史的深厚感情和思考;對經(jīng)典作品的改編、融入新元素,可以讓當(dāng)下的音樂受眾更好地欣賞作品,在流淌的旋律中實現(xiàn)同頻交流。
我進(jìn)入中國歌劇舞劇院工作以來,在《小二黑結(jié)婚》《江姐》《白毛女》等紅色經(jīng)典歌劇重排的工作中,得到了大量學(xué)習(xí)和鍛煉的機(jī)會。也將這些積累和升華傾注在了剛剛和前輩作曲家合作完成的歌劇《唱響南泥灣》之中,榮幸與不安同在。以閻肅、羊鳴老師為代表的第一代紅色經(jīng)典歌劇的初創(chuàng)者,他們成長于革命年代,對那段歷史有切身的體會。那么,作為后輩的我們在新時期如何做到守正創(chuàng)新?
于是,在原作的基礎(chǔ)上,我們進(jìn)行了唱段改編,對“服化道”進(jìn)行創(chuàng)新,與優(yōu)秀的作曲家、優(yōu)秀的演員們一起碰撞打磨,走進(jìn)歷史,感受劇中人物的信仰和身處其時的選擇與決心,以當(dāng)代觀眾更能直觀理解的方式表現(xiàn)紅色革命故事,帶他們深入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發(fā)展過程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過程中的那段艱難的成長史,以及為此付出巨大犧牲與無私奉獻(xiàn)的革命英雄,喚起聽眾對經(jīng)典之聲的集體記憶。
從2014年開始,我逐漸開始參加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等國家級的大型主題創(chuàng)作活動。回首一程,我深感自己的創(chuàng)作過程也是見證國家富強(qiáng)和人民生活變化的過程。
2021年12月,我有幸作為新文藝群體的一員參加了中國文聯(lián)第十一次文代會,現(xiàn)場聆聽了習(xí)近平總書記對文藝事業(yè)發(fā)展和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寄語。
我要感謝這個美好的時代,時代給了我一支筆,讓我有機(jī)會以音樂來表達(dá)對身處盛世的熱愛與思考;感謝可愛的人民,是他們多姿多彩的生活不斷激發(fā)著我的創(chuàng)作熱情。我相信,如此廣闊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也會滋養(yǎng)出更多優(yōu)秀的“后浪”音樂人,我對未來充滿期待!
楊一博,中國歌劇舞劇院駐院作曲家,音樂制作人,中國文聯(lián)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聯(lián)青年文藝創(chuàng)作扶持項目評委,擔(dān)任過多部歌、舞、器樂、國家級大型紀(jì)念活動、專題文藝晚會的音樂總監(jiān)及主創(chuàng)。 主要作品有第一交響曲《渡江—1949》、管弦樂《樂動阿勒錦》《山高水長》、民族管弦樂《水潤萬寧》、歌劇《唱響南泥灣》(合作)、舞劇《英雄兒女》《劉胡蘭》、音樂劇《大道無垠》、電影音樂《我的父親焦裕祿》、歌曲《多想對你說》《無名花》等。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提名,“國家藝術(shù)基金”“中國夢”展播歌曲創(chuàng)作者等獎項。
點(diǎn)擊下圖購買《中國青年》2022年第18期
《中國青年》雜志2022年第18期 《經(jīng)典 青春 夢想》 總監(jiān)制:皮鈞 郝向宏 總策劃:藺玉紅 冉茂金 總統(tǒng)籌:楊玳婻 張斯絮 韓冬伊
監(jiān)制:皮鈞 終審:藺玉紅 審校:張斯絮 劉曉 劉博文 本期紙刊封面設(shè)計:荷青 微信封面橫圖設(shè)計:高涵 編輯:許博文(實習(x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