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倪匡——寫作
《今夜不設(shè)防》最后一期,沒有請嘉賓。
取而代之的是,香江三大名嘴黃霑、倪匡、蔡瀾的互訪閑聊。
由于之前的訪談中,倪匡總喜歡搶話,所以這次大家決定,一定要先讓倪匡聊個夠。
“倪匡,你當(dāng)初怎么會入行寫東西呢?”黃霑一上來便問道。
每當(dāng)問及這個問題時,倪匡的回答總是出奇的一致:
“我沒有其他本事的!”

倪匡稱,自己初到香港時,七十二行自己差不多做了三十六行。
做雜工,擔(dān)泥,修馬路,幾乎什么都做過。
“你還修過馬路嗎?”黃霑完全不敢相信。
倪匡滿臉不屑道,
“全香港的馬路我都修過。因?yàn)樾揆R路的工資高啊,一天有八塊錢。
其他工作只有三塊六,還要被工頭克扣。”

倪匡回憶稱,自己初到香港時,在荃灣那邊,四十幾個人住在一起。
大家都是從大陸來的,很抱團(tuán),一起工作一起吃飯。
比如今天工頭來,只要二十二個人,這二十二個人就去工作。
其他人沒地方去,只好留在原地。
等到晚上,這二十二個人拿錢回來,再一起去吃飯。
有時候錢不夠吃飯,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喝得飽?”蔡瀾問道。
“有糖呀!”倪匡笑瞇瞇稱
“糖不要錢的,當(dāng)然拼命下了。我到現(xiàn)在喝咖啡,還是會下很多塊方糖的。”

倪匡的第一篇投稿,就是在這時候?qū)懙摹?/p>
當(dāng)時倪匡沒有被挑去開工,只好待在原地,等其他人回來拿錢吃飯。
閑的時候,就看報紙。
報紙副刊上有篇萬言小說,每周更新一次。
倪匡邊看邊說,
“這種東西,我也會寫。”
沒有人相信,倪匡就花了兩個下午寫給他們看。
這也是倪匡的第一篇小說,講述地主子女遭遇的《活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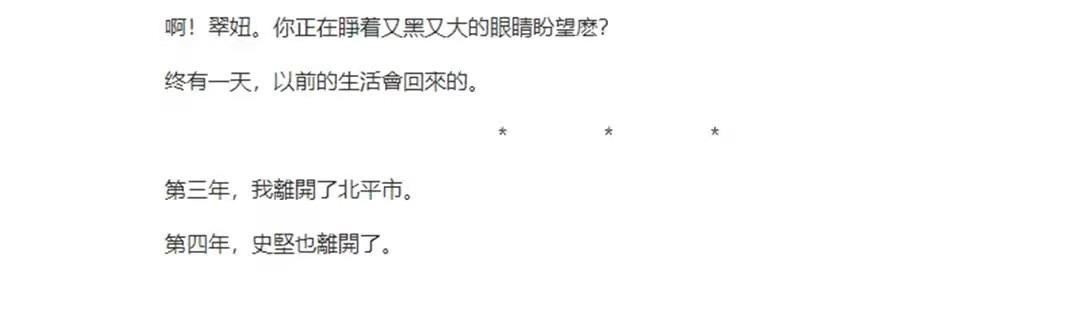
倪匡寫完,選了家最保守的報紙《工商日報》投稿。
幾天后,編劇找到倪匡,說可以用他的稿,稿費(fèi)是九十塊錢。
講到此處,倪匡再也按耐不住激動的心情,眉飛色舞道:
“我真的笑傻了!我兩個下午寫出來就有九十塊稿費(fèi),太劃算了。
那可是兩塊九毛錢就能吃四碗叉燒飯的年代啊!”

嘗到甜頭后,倪匡開始四處投稿,影評、雜文什么都寫。
倪匡自負(fù)稱,說也奇怪,在我記憶中,真的沒有被人退過稿。
在給《真報》投雜文時,并沒有稿費(fèi)。
他們說報館太小,付不出錢來。倪匡毫不介意,反正閑著,權(quán)當(dāng)練筆。
后來投得多了,報館過意不去。就讓倪匡去報館幫忙,當(dāng)副編輯助理。
“哈哈哈,副編輯助理?!”黃霑大笑道。
倪匡一臉滿足道:
“月工資給一百三十塊呢,分兩期給,我又笑了三天。”
(倪匡早期的辛酸,黃霑和蔡瀾自然是體會不到的)

“接著呢?接著呢?”已聽上癮的黃霑,迫不及待得追問道。
倪匡稱,之后就是一邊工作一邊寫稿了。
突然之間,有個武俠小說名家在《真報》斷稿了,報館讓我續(xù)寫。
“哪個武俠小說名家?講出來啦!”黃霑好奇道。
倪匡頓了頓,講道,
“司馬翎嘛!他寫的小說很好,只不過當(dāng)時斷稿了。”
就這樣,倪匡替司馬翎寫了一個星期。
司馬翎回來一看,發(fā)現(xiàn)小說和自己的構(gòu)思出入很大,干脆不寫了。
倪匡只好寫完了那篇小說,結(jié)果卻大受好評。
此后,《真報》給倪匡開了一個專欄,專門寫武俠小說。

《真報》對倪匡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跳板。
正是這段經(jīng)歷,讓倪匡獲得了工作近三十年的老東家《明報》的賞識,自此揚(yáng)名中外。
“那時你的筆名還不叫倪匡吧?”黃霑好奇道。
“是倪匡!寫武俠小說時已叫倪匡。”倪匡答道。
“是嗎?你不是有個筆名叫岳川嗎?”
“岳川是以后的了。”
倪匡創(chuàng)作力十分旺盛,筆名也取過不少。
“岳川”的由來,是因?yàn)槟呖镌凇睹鲌蟆吠瑫r連載兩篇武俠小說。
所以一定要取兩個不同的筆名才行。
期間,倪匡還在《真報》寫雜文,“衣其”和“沙翁”是其寫雜文時的筆名。
聽到此處,黃霑感嘆道:
“衣其我看過!火爆的不得了!名氣火過沙翁!”

當(dāng)然,倪匡的筆名還遠(yuǎn)不止于此。
“阿木”、“魏力”、“倪裳”、“九缸居士”…都是倪匡用過的筆名。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還要屬:衛(wèi)斯理。
當(dāng)時,倪匡在《明報》已連載兩篇武俠小說,要連載第三篇,所以還要取一個筆名。
“衛(wèi)斯理”也由此而來。
(江湖傳言,倪匡最高記錄:每天有十二篇連載小說,四五個專欄)
倪匡的衛(wèi)斯理系列小說,最初的定位是“現(xiàn)代武俠”。

1963年,在倪匡動筆前,《明報》還特意為其做了廣告:
“衛(wèi)斯理先生是一個足跡踏遍全球的旅行家,又是一個深精武術(shù)的名家。
本報請衛(wèi)先生所撰的小說,熔武俠、言情、探險小說之優(yōu)點(diǎn)于一爐。
情節(jié)曲折緊張,高潮疊起,描寫愛情之細(xì)膩,故事之新奇,保證為香港報章上所從來未見…”
不過,倪匡在寫了兩篇后,發(fā)現(xiàn)讀者反應(yīng)一般,遠(yuǎn)沒有自己的武俠火爆。
所以,在第三篇時,倪匡建議轉(zhuǎn)為幻想小說。
“什么叫幻想小說?”金庸問倪匡。
“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完全天馬行空,毫無規(guī)章可循。”
金庸聽后,竟然同意了。

據(jù)倪匡講,轉(zhuǎn)為幻想小說后,依舊不溫不火。
一直到10年前(1980年),才開始被大眾接受。
“所以我有時候很自負(fù),我走在時代前沿好多,差不多領(lǐng)先二十年。”倪匡緩緩道。
說起“衛(wèi)斯理”的由來,倪匡稱,自己取名的本事很差。
當(dāng)時,恰巧坐巴士經(jīng)過大坑道,沿途有個村子叫:“衛(wèi)斯理”。
所以,干脆將自己的筆名取名“衛(wèi)斯理”了。
當(dāng)然,在倪匡眼中,衛(wèi)斯理還有另一層含義,即“保衛(wèi)道理”的意思。

02、蔡瀾——電影
“蔡先生有一句話,說我們?nèi)齻€人山水相投。”黃霑介紹道:
“倪匡今天已經(jīng)講得夠多了,現(xiàn)在該你了,蔡瀾,你怎么會進(jìn)電影行的呢?!”
蔡瀾初時興致不高,可能是沒有美女嘉賓的緣故。
“很自然就入行了。我不喜歡講回以前的事的…”蔡瀾在一旁有氣無力道。
“不喜歡講也要講了,因?yàn)橛^眾有興趣知道啊!”倪匡插話道。
黃霑不愧是主持大佬,開始了循序善誘的套路,直接問道:
“你怎么會去日本讀書呢?你留學(xué)日本八年的嘛!”

蔡瀾見躲避不過,扭捏說道,
小時候,我媽喜歡喝酒,我也喝酒。
我小時候?qū)W得是畫畫那些,最想去的地方是法國,我喜歡去那個地方畫畫。
(原來蔡瀾最初的夢想是當(dāng)一名畫家)
但是母親不同意我去法國,在她眼里,法國人個個是酒鬼。
于是,去了日本。
“她不知道,其實(shí)日本人也喜歡喝酒的”蔡瀾無奈道。
眾人聽后大笑。

說回入行電影的經(jīng)歷,蔡瀾稱,
自己很小時候就喜歡看電影,因?yàn)楦赣H的關(guān)系。
“我父親是電影院的經(jīng)理來的,我的家就住在一家電影院的三樓。”
“直接住在電影院里了”黃霑大笑道:
“那你不做電影都很難的。”
蔡瀾稱自己的父親是電影院的經(jīng)理,實(shí)在是太過謙虛了。
蔡瀾之父蔡文玄,字石門。實(shí)為邵氏公司最大的元老。

當(dāng)時,邵氏由上海出發(fā),企圖遍布整個東南亞。
老二邵邨人進(jìn)香港,老三邵仁枚入南洋,也就是現(xiàn)在的新加坡。
邵仁枚到新加坡后,開始只是拿著皮包機(jī)到處放映電影。
后來租到戲院,急需幫手,便從上海調(diào)來了兩個人,
一位是邵氏家族的六弟,也就是邵逸夫。
另一位就是蔡瀾之父,蔡文玄。
可想而知,蔡瀾的父親在邵氏的資歷有多老。
難怪連大導(dǎo)演李翰祥都稱,
蔡瀾的父親是邵氏除三老板和六老板這對兄弟以外的,最大話事人。

黃霑想必也知道此節(jié),故意問道:
“有一個江湖傳說,現(xiàn)在要跟你證實(shí)一下,
據(jù)說邵逸夫幫過你去日本留學(xué),有沒有這回事?”
“也不是”蔡瀾緩緩道:
“開始是家里人讓我去,去了以后我就半工讀。
當(dāng)時我又打邵氏的工,是邵氏駐日本的代表。
就是這樣子啊!我的生命很普通的,沒有那么曲折。”
蔡瀾似乎并不愿多講往事,也不喜歡談邵氏。
可能蔡瀾和邵氏之間有過一些不為人知的不愉快的事。
不然,蔡瀾也不會在離開邵氏后,直接去了邵氏的死對頭嘉禾,去當(dāng)制片了。

倪匡見蔡瀾興致不高,特意講了蔡瀾一段笑話。
話說蔡瀾曾替邵氏去日本談判,期間,蔡瀾裝作不懂日語,故意帶了翻譯去。
談判時,翻譯全程跟翻。
等到快結(jié)束時,蔡瀾給翻譯使眼色,讓其去廁所。
翻譯走后,那幾個日本代表以為蔡瀾聽不懂日語,便大膽探討戰(zhàn)略。
結(jié)果,說的悄悄話都被蔡瀾聽得正著。

黃霑一心想讓蔡瀾多聊一些,又問道:
“你監(jiān)制了這么多電影,最喜歡哪一部?”
“沒有哪一部,下一部咯!”蔡瀾依舊興致不大。
“導(dǎo)演呢?你最喜歡哪個導(dǎo)演?”
“下一個導(dǎo)演咯”蔡瀾繼續(xù)道:
“這些話題都好悶的,不喜歡電影的人,聽我們聊這些感覺太專業(yè)了。”
“女明星呢?!”黃霑大聲的斬釘截鐵得問道。
“下一個咯”
黃霑無奈之極,最后緩緩道:
“那你有沒有后悔進(jìn)入電影行業(yè)?”
“沒有后悔,每一分鐘我都中意,都很享受”

倪匡插話道:
“我也不后悔的,我很中意寫作的,很中意很中意”
蔡瀾見此,知道機(jī)會來了,趕忙對黃霑講道:
“你呢?”
03、黃霑——填詞
講回自己,黃霑稱,自己也很喜歡寫作的。
除“黃霑”以外,自己還有另外一個筆名叫“亦芹”。
有些人知道后,會說又叫“黃霑”又叫“亦芹”,這不是在說自己是曹雪芹嗎?
“中國有兩霑嘛,一個曹霑,一個黃霑”倪匡在一旁起哄道。
(曹雪芹原名曹霑,號雪芹)
“不是的”黃霑解釋稱:
“是我有一個叫芹的二姐的緣故。
她曾經(jīng)是廣東一個學(xué)校的校長,現(xiàn)在已經(jīng)退休了,每月拿160塊人民幣退休金。
我之前去看她,很威風(fēng)的,很多高干都曾是她的學(xué)生。”

說到自己寫歌,黃霑稱,自己很中意寫歌的。
但有一件事很痛苦。
本來寫歌只是嗜好來的,很開心。
后來,由嗜好變成工作時,痛苦也就隨之而來了。
因?yàn)閷⒅暈楣ぷ鞯脑挘憔鸵煌5倪M(jìn)步,對自己的作品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苛刻。
這樣一來,就變得不是很快樂了。

黃霑回憶道,
自己第一次做配樂,是在又一村花圃街,
給胡楓和蕭芳芳主演的電影《歡樂滿人間》做音樂。
那是自己第一次指揮樂隊,玩自己寫的歌,感覺非常開心。
當(dāng)時酬金有2000塊,我卻花費(fèi)了1950塊請樂隊。
一部電影寫了九首歌,最后算下來,只賺了50塊錢。
但是很開心。
我直接躺在地毯上,聽樂隊演奏,感覺很舒服,很滿足。
由回憶返回現(xiàn)實(shí),黃霑稱,
自己現(xiàn)在寫歌賺的錢,當(dāng)然不止這個數(shù)了。
但是寫完錄完,一演奏,卻發(fā)現(xiàn),這個也不喜歡,那個也不喜歡。
快樂感少了很多。

“很多年之前,我還不怎么認(rèn)識他的時候,
他就已被封為粵語流行曲之父。”倪匡指著黃霑向蔡瀾稱贊道。
“多謝你,倪匡”
黃霑邊戴墨鏡,邊脫西服解領(lǐng)帶,邊對倪匡講。
倪匡意猶未盡,繼續(xù)道,
粵語流行曲是從他《問我》這首歌開始的,到現(xiàn)在這首歌仍是經(jīng)典。
用方言能把一首歌的歌詞,填得那么有文化,
到現(xiàn)在為止,也只有《問我》一首。
此時黃霑已整理就緒,袖口已挽好,領(lǐng)口上的扣子已解開,人也坐到了地上。

“說起《問我》呢,是有個故事的”黃霑開口了。
當(dāng)時是亞視的前身“麗的電視”的音樂主任黎小田先生,
寫了一首歌,用作電影《跳灰》的主題曲。
找我寫歌詞,我寫了四份歌詞都不喜歡,被人罵得很慘,都丟掉了,
交貨時間要到了,又有這么多人罵我,怎么辦呢?于是: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
問我悲哭聲有幾多
我如何能夠
一一去數(shù)清楚
問我點(diǎn)解會高興
究竟點(diǎn)解要苦楚
我笑住回答
講一聲 我系我
面對世界一切
那怕會如何
全心去承受結(jié)果
就算我有百般對
或者千般錯
全心保存真的我
愿我一生去到終結(jié)
無論歷盡幾許風(fēng)波
我仍然 我仍然
能夠講一聲
我系我
(此為黃霑現(xiàn)場即興演唱歌詞,和原版歌詞有出入)

黃霑繼續(xù)道,黎小田看到后,很喜歡。
他當(dāng)時在麗的電視主持《家燕與小田》,就現(xiàn)場唱了出來。我都不知道。
第二天,華娃(黃霑的第一任妻子,當(dāng)時已分居)打電話來,問黃霑,
“昨晚黎小田唱的那首歌是不是你寫的?”
“什么歌啊,我沒看那個節(jié)目。”
“就問什么問什么那首”
“是啊!是啊!”
講道此處,黃霑頗為自豪,向倪匡、蔡瀾解釋稱,
當(dāng)時黎小田在節(jié)目中,并沒有提到我。
但她卻能猜到是我。
她說,全香港我認(rèn)識的填詞人,沒幾個能寫得出這樣的歌詞。
也只有你這個衰仔了。
(不得不說,最了解黃霑的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黃霑輕嘆一口氣,忽又反問倪匡
“你真的很中意我的《問我》啊”
“很中意很中意,無論詞還是曲,都很中意,
我覺得這首歌是經(jīng)典歌,幾百年后仍會流行。”倪匡答道。
黃霑調(diào)侃稱,那你先讓你的兒子倪震學(xué)會唱再說。
倪匡又一次激動道:
“自從這首歌之后,粵語歌才開始流行的,本來粵語歌已經(jīng)消失了。”
這時,黃霑謙虛起來,緩緩道:
“不能這樣講,許冠杰有幾首也挺好的。”

“繼續(xù)講你自己啊,《問我》以后,怎么開廣告公司了?”倪匡也變得好奇起來。
黃霑稱,寫《問我》的時候,已經(jīng)在開廣告公司了。
當(dāng)時,我跟林燕妮各出兩萬港幣。
“才兩萬塊,就能賣給別人幾千萬啊?!這么好賺得嗎?”倪匡驚訝道。
(指1986年,黃霑的“黃與林”廣告公司被盛世收購)
“我們當(dāng)時挨得很辛苦啊”
“大佬,才十年八年而已嘛!”
黃霑回憶稱,廣告公司前幾個月一個客戶都沒有的,
直到第七個月,才接到一筆大單。
“是一款很老牌子的白蘭地。”黃霑笑稱
(這里指軒尼詩。軒尼詩經(jīng)典廣告詞:“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便是黃霑寫于此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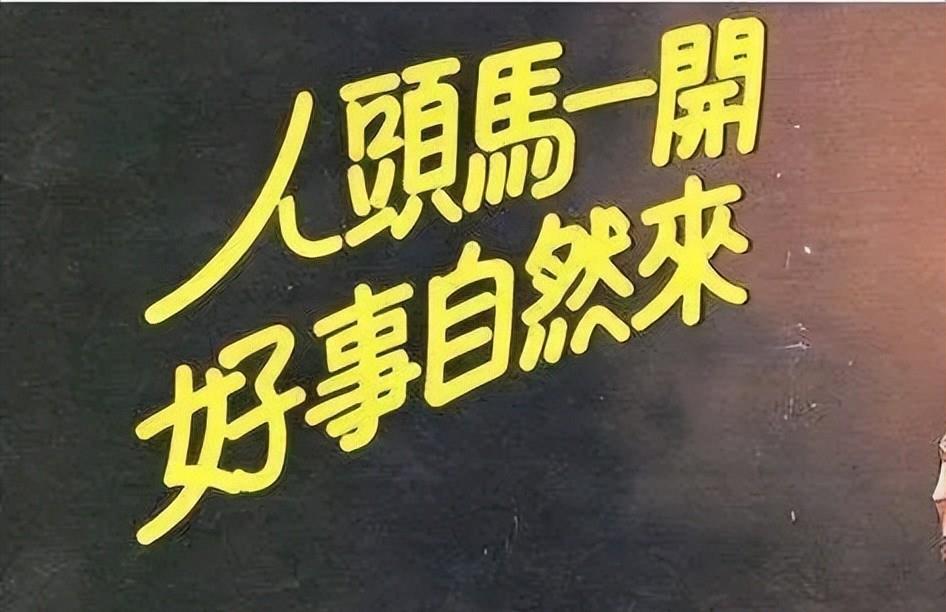
在三人的嬉笑聲中,節(jié)目也到了尾聲。
雖然這期沒有請大咖嘉賓,但這三人,哪一位又不是真正的大咖!
三人所處行業(yè)雖不同,背后的故事卻都精彩紛呈。
你更喜歡誰多一些呢?
往期精彩:
倪匡早年的逃亡之路,大雪之夜騎馬狂奔,倪匡:今天做夢都會夢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