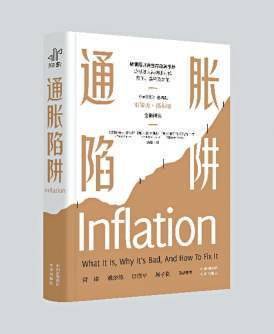
《通脹陷阱》 史蒂夫·福布斯 內(nèi)森·劉易斯 伊麗莎白·埃姆斯 著 中譯出版社
全球經(jīng)濟(jì)正亟待走出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困頓,又遭逢嚴(yán)重通貨膨脹的沖擊。《通脹陷阱》得以在本輪通脹的暴風(fēng)眼——美國(guó)出版,并被翻譯給廣大的中國(guó)讀者,可謂正得其時(shí)。
從通貨緊縮到通貨膨脹
20世紀(jì)末21世紀(jì)初,“通縮”成為世界性經(jīng)濟(jì)話題。彼時(shí),關(guān)乎通貨緊縮的研究與預(yù)判成為醒世恒言,而非“通脹”。
1999年,保羅·克魯格曼在美國(guó)《外交事務(wù)》雜志上發(fā)表一篇題為《蕭條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回歸》的文章,并出版了同名著作;同年,加利·西林出版了《通貨緊縮》一書。2004年,本·伯南克出版了其名著《大蕭條》,宣稱“大蕭條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圣杯”。
2008年,金融海嘯襲來,量化寬松(QE)成了救世的急猛之藥,“大水漫灌”遍及東西方。伯南克和鮑威爾兩任美聯(lián)儲(chǔ)主席分別于2013年和2019年試圖終止QE未果。2021年6月,美國(guó)出現(xiàn)通貨膨脹的警訊,但貨幣當(dāng)局堅(jiān)持認(rèn)為,通脹是暫時(shí)的;半年后,美聯(lián)儲(chǔ)被迫改弦更張;2022年5月,美財(cái)長(zhǎng)耶倫公開“認(rèn)錯(cuò)”:未能及時(shí)判定通脹情勢(shì)。
這一期間,伯南克甚至被指責(zé)為本輪通脹的始作俑者。全球范圍內(nèi)對(duì)產(chǎn)業(yè)鏈?zhǔn)苷卧驔_擊而斷裂的擔(dān)憂,又引發(fā)價(jià)格的進(jìn)一步上漲。在希望中國(guó)持續(xù)輸出更多廉價(jià)商品的同時(shí),西方輿論中的某些雜音又出現(xiàn)了——只不過,他們這次不擔(dān)心中國(guó)輸出通縮,而是憂慮中國(guó)因其自身經(jīng)濟(jì)恢復(fù)而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
時(shí)移世易,抑制“通脹”已成為當(dāng)前世界經(jīng)濟(jì)的主旋律。《通脹陷阱》或許可為中國(guó)讀者們解惑答疑。
通脹三問
通脹關(guān)乎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中的每一個(gè)人,遠(yuǎn)不應(yīng)限于書齋,更不宜局限于抽象的概念或者善惡好壞的評(píng)斷,而應(yīng)從廣泛而真切的事實(shí)中帶入,“詞簡(jiǎn)理博”地透徹闡釋通貨膨脹的本質(zhì)和內(nèi)涵,引發(fā)讀者的共鳴。坦言之,史蒂夫·福布斯于此做了很好的嘗試。
本書從“通貨膨脹”發(fā)展的歷史脈絡(luò)推展開來,從兩千年前的羅馬皇帝尼祿一直談到了當(dāng)下的美聯(lián)儲(chǔ),既示警于中央銀行,又予個(gè)人以投資建議。概言之,本書提出并試圖回答通貨膨脹“是什么”“為什么發(fā)生”“怎么應(yīng)對(duì)”三個(gè)問題,讀來輕松,感觸良多。
從經(jīng)驗(yàn)來看,不同時(shí)代或不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體系下,通脹狀況各有不同,人們的現(xiàn)實(shí)感受也有所不同。于是乎,少量通脹有助于就業(yè)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政策主張及實(shí)踐就發(fā)生了。作者將支持通脹政策的主張列入形形色色的凱恩斯主義,有其邏輯所在。回到貨幣標(biāo)準(zhǔn)穩(wěn)定性而言,本書主張從絕對(duì)意義上反對(duì)通貨膨脹,視通脹為絕對(duì)的“惡”,而不計(jì)其大小。這一立場(chǎng)宜廣泛汲取。21世紀(jì)之初,有人欣喜于所謂“好的通貨緊縮”,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有人激賞中央銀行激進(jìn)的通脹政策,更有人禮贊所謂的“現(xiàn)代貨幣理論”(MMT)。稍加時(shí)日,惡果自彰,便發(fā)現(xiàn)其只是飲鴆止渴。
其次,警惕飲鴆止渴。通貨膨脹歸根結(jié)底是貨幣現(xiàn)象,同貨幣供給關(guān)系密切。沒有中央銀行的“大水漫灌”,供過于求的貨幣態(tài)勢(shì)極難發(fā)生。現(xiàn)代惡性通貨膨脹的發(fā)生,往往離不開中央銀行的主動(dòng)作為。癥結(jié)不在于中央銀行這一所謂的“中心化”機(jī)構(gòu)自身,而在于其政策取向。《通脹陷阱》一書歷數(shù)了美國(guó)偏好擴(kuò)張貨幣供給的現(xiàn)代“通貨膨脹主義”的惡性案例,并不遺余力地聲討之,表明了作者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上都是徹頭徹尾的反通脹者。
第三,回歸金本位制是解決之道嗎?書中指出,黃金價(jià)格及其變化可作為檢驗(yàn)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biāo)。引申開來,這是檢驗(yàn)所謂“貨幣性”通脹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更是所謂“貨幣腐敗”的照妖鏡。在如何應(yīng)對(duì)通貨膨脹的問題上,作者堅(jiān)信回歸金本位制是必然之選,這值得各位讀者深入思考。
應(yīng)當(dāng)說,回歸金本位制的貨幣主張不僅在美國(guó)一直有其代表,而且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不罕見。究竟應(yīng)在何種意義或程度上回歸金本位制的意見或有不同,但每逢貨幣情勢(shì)危殆之時(shí),回歸金本位制的聲音便格外響亮,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對(duì)此也習(xí)以為常。
有人給回歸金本位制的主張貼上了“反革命”的標(biāo)簽,貼標(biāo)簽者自身倒是不自覺地以“革命者”自居,實(shí)則像極了貨幣“造反派”。這就不難發(fā)現(xiàn),如若一路“革命”下去,不僅黃金不得復(fù)活,“通貨膨脹目標(biāo)制”更要大行其道。進(jìn)而,通過奉行所謂的“現(xiàn)代貨幣理論”,中央銀行的獨(dú)立性將受到威脅。他們甚至還會(huì)要求廢止“中心化”的中央銀行,發(fā)行并運(yùn)行“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以此全面代替銀行貨幣體系……
自貨幣誕生以來,已有數(shù)千年歷史。自然形態(tài)的貨幣歷史難以溯源,人工形態(tài)的金屬貨幣時(shí)代約三千年,紙幣約一千年,賬戶形態(tài)的銀行貨幣不足4個(gè)世紀(jì),數(shù)字形態(tài)的貨幣剛剛呱呱墜地……貨幣形態(tài)的革命步伐似乎加快,但貨幣代際的繼承性和連續(xù)性卻緊密相連,未曾割裂。所謂貨幣的“革命”或“反革命”,信口開河而已,姑妄聽之,當(dāng)不得“真”。盡管如此,復(fù)辟舊貨幣形態(tài),往往使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遭受重大挫敗,泥古、復(fù)古的貨幣嘗試終究也未見其功,甚至反受其害。新與舊之間,貨幣的穩(wěn)定基于繼承性和連續(xù)性。
近幾個(gè)世紀(jì)以來,黃金漸漸成為貨幣的準(zhǔn)繩,與其說是“(價(jià)值)保障”,不如說是“(紀(jì)律)約束”,即任何形態(tài)的貨幣退出流通貨幣體系,須給付所承諾的“對(duì)價(jià)”。作者在本書中所一再?gòu)?qiáng)調(diào)的貨幣“標(biāo)準(zhǔn)”及“信任”,正是根植于此。
在關(guān)乎計(jì)量、發(fā)行、流通、結(jié)算的諸個(gè)環(huán)節(jié)中,黃金從來不是最好的貨幣安排,但也絕非貨幣惡亂之源。金本位制所標(biāo)榜的是貨幣的紀(jì)律約束。要不要回歸金本位制的問題,本質(zhì)上是要不要有效的貨幣紀(jì)律約束的問題。對(duì)此,答案是肯定的。具體什么樣的貨幣紀(jì)律約束才是根本有效的,的確值得人們不斷地探討與深入地省思。
美國(guó)貨幣當(dāng)局一直是當(dāng)今世界最大的黃金資產(chǎn)儲(chǔ)備擁有者。近年來,俄羅斯、土耳其、中國(guó)、印度等各國(guó)的央行正不斷地“扎堆兒”增持其黃金資產(chǎn)儲(chǔ)備。將黃金完全排斥在貨幣體系相關(guān)安排之外是不現(xiàn)實(shí)的,更是徒勞的;而全面蔑視甚至完全摧毀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對(duì)黃金的“貨幣信念”則是裝腔作勢(shì)、狂妄自大的。
陷阱何在
彭信威先生在其名著《中國(guó)貨幣史》中曾提及,西方更關(guān)注通貨緊縮,而中國(guó)更關(guān)心通貨膨脹。換言之,通脹相較通縮,西方更厭惡后者,而東方更仇嫌前者。此亦無他,囿于各自所處的不同時(shí)代歷史境遇而已。但若一定要在通脹或通縮間分出伯仲,或者主張所謂“好的通縮”或“好的通脹”,便出離了經(jīng)濟(jì)理性,淪為十足的“戀愛腦”了。
因時(shí)適變,是貨幣歷史演進(jìn)、發(fā)達(dá)與成熟的根本所在。
如何在適變中保持貨幣標(biāo)準(zhǔn)的穩(wěn)定?這正是史蒂夫在本書中所一再?gòu)?qiáng)調(diào)的題眼所在。離開了貨幣計(jì)量標(biāo)準(zhǔn)的穩(wěn)定,任何精美的理論或高妙的政策都不免終將落入“陷阱”之中。事實(shí)上,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通縮的一面苦辣而咸,通脹的一面初嘗起來甚至像蜜糖一樣甜膩膩,更具誘惑性。然而,通脹往往導(dǎo)致通縮政策,甚至未及通縮便因惡性通脹導(dǎo)致貨幣崩潰。
(作者為浙江現(xiàn)代數(shù)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長(zhǎng))
(原標(biāo)題:沒有所謂“好的通貨膨脹”)
來源:北京日?qǐng)?bào) 作者 周子衡






